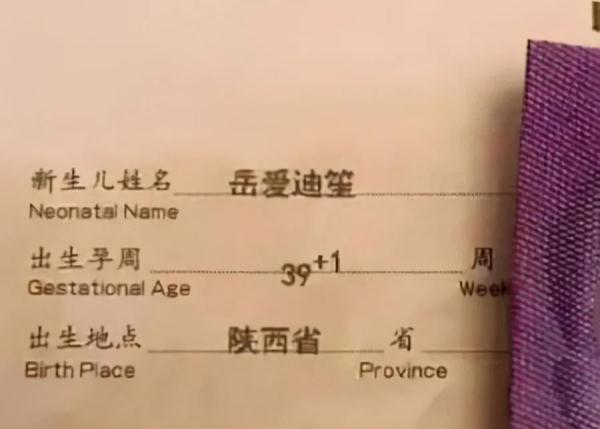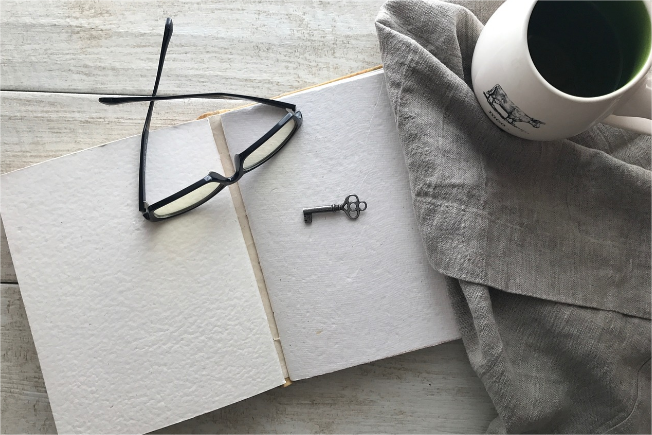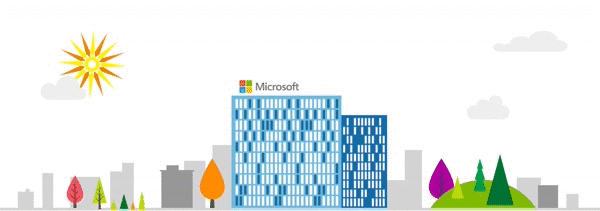江城子记梦情感-江城子记梦基本思路步骤
时间:2024-06-26人气: 作者:佚名
2008年10月第8卷第5期 鸡西大学学报 鸡西大学学报 V01.8 No. 5 Oct. 2008 文章号: 1672-6758 (2008) 05-0112-4 史上第一首挽歌的经典化进程——《江城子·梦》接受视角的历史演变 刘德 摘要:中国古代悼亡文学具有强烈的生命力,尤其是诗和词。悼亡词的开山之作是苏轼的《江城子·梦》。这部词虽然有近千年的影响历史,但却长期被词评家所忽视,只有近百年的影响和诠释历史。这部词之所以被长期埋没,是因为它的思想超越性、审美的先进性和写作风格的独特性。 直至20世纪,随着学界对该诗的主题、背景、风格、语调等进行考察,对其认识不断加深,最终将其推崇为“千古第一悼亡诗”,从而完成了“经典化”的过程。・关键词:悼亡诗;悼亡诗;超越;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:1207.23 文献标识码:A 悼亡诗、悼亡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十分特殊的作品。《诗经》中的《青衣》是中国悼亡艺术的雏形。晋代诗人潘岳为追思亡妻而作《悼亡诗》后,悼亡便成为“悼亡妻”的专利。 后期悼亡作品中,以唐元稹《送愁三首》、宋苏轼《江城子·梦录》、清纳兰性德《金缕曲》成就最高。苏轼《江城子·梦录》为第一首悼亡诗,诗人用灵活的文笔,真实地表达出“唯有万千泪”的凄惨灵魂,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纵观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发展,礼制的制约,使这类作品的接受变得异常艰难;尤其在“诗以庄严,词以韵致”的古代传统下,“悼亡词”的接受速度比“悼亡诗”慢,苏轼悼亡词也很少受到古代词评家和词选家的重视。但历代诗人却十分喜爱,创作了大量悼亡词,所以这首词有着近千年的影响史。近千年的创作影响史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去想,忘不掉。千里孤坟,无处说凄凉。纵使相见,也应不相认,满面尘土,发如霜。夜来,恍然梦回故乡,窗外小窗。 我正梳妆打扮。相视无语,唯有泪眼婆娑。我料想,每年令我心碎的地方,是月夜的矮松丘。苏轼的《江城子·梦》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,此时是其妻王弗去世十年后。全诗结合了他仕途坎坷的感受,抒发了对亡妻的哀思,写得情深意切。此诗自发表后,立即引起诗人们的共鸣,纷纷在上下文、文体、意象、曲调等多方面加以效仿,开创了悼亡诗的兴盛。1、上下文的悲情。恩格斯说:“最崇高、最强烈、最个人的痛苦,是爱情的痛苦。” 所以,以爱情为经,以死亡为纬,文人所编织的悼亡诗词,就带有一种悲情色彩。面对无情的现实,苏轼巧妙地营造了梦境,通过梦前的思绪、梦中的情感交流、梦醒后的悲凉,完成了多层次的情感体验,增强了诗的悲情色彩。
正如王夫之所言:“以喜景写悲,以悲景写喜,悲喜倍增。”诗人虽然也知道阴阳有界限,但他坚信爱情是没有界限的。诗的结尾,诗人不从自己出发,而是从亡妻身边出发,抒发思念之苦。永恒的思念在月光下定格,让人唏嘘不已。被王夫之赞誉为“北宋以来独一无二”的纳兰性德,受苏轼影响最大,一生写下50首悼亡诗,是苏轼之后悼亡诗的集大成者。其代表作《沁园春》“借”苏轼的诗境,完成了一场梦中的幽会。 梦前的苦涩相思为诗人的叹息埋下了伏笔,而诗人“梦中难留”的叹息,则是诗人梦醒之后惆怅心情的真实再现。“再寻那苍茫碧空,期盼清晨短发霜雪”,深受苏轼“期盼年年心碎的地方,月夜短松岗”诗句的启发。总之,那借苏轼诗句的梦境,将历史与未来以梦嫁接。通过梦前的寻觅、梦中的相会、梦后的远眺,将情感在不同的时间横断面中展现得悲壮,增强了悼亡诗的感染力。2、写作方法的独创性。 在历代悼亡作品中,丈夫总是通过琐碎小事来表达对亡妻的哀思,让亡妻成为被动的“接受者”。这种单向的情感辐射的表达效果毕竟有限。但苏轼不同。《生死十年》,诗人将妻子视为平等的人。他打破阴阳的隔阂,穿越时空,前去寻找挚爱的亡妻。作品中,“满脸尘土”的诗人与“妆点得漂漂亮亮”的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,为双方的情感平等交流提供了平台。
诗人思念亡妻,亡妻以真挚的情意回报他的爱。“我料想,每年我都会在月夜里,在一棵矮松岗上,痛痛快快地哀悼亡妻。”亡妻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。这种双向的情感辐射,增强了作品的穿透力。正如顾敬之所说:“他们(指过去写悼亡诗的诗人)的共同之处,都是从生者的角度去写怀念亡妻,抒发哀痛之情,但像东坡这样短小的诗篇,却没有生者与亡者的情感交流。”诗人以“思念某人”的情感来悼念亡妻,这是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。何焯的《半死桐树》与苏轼的诗有相似的写作风格,即都用“思念某人”的方式来悼念亡妻。 诗以悲凉悲壮的语调开头:“再过关头,一切都已过去,我们同时来,却不会一起回来?”诗人在深深叹息的同时,也在质问亡妻。这略带责备的语调,是诗人情绪的井喷。“平原上的草儿开始叹露,旧巢新巢两相依。”作品通过新巢与旧巢的并置,“两相依”的情感联系,将诗人与亡妻之间的相互依恋与交流表达得淋漓尽致,增强了艺术感染力。 顾敬之指出:“悼亡诗的艺术感染力在于,死者不仅是生者追忆的对象,更是生者继续情感交流的对象,构成了生者与死者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超凡境界;也正因为这种境界的‘超凡’,才凸显了作者简介:刘德,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生,安徽芜湖,研究方向:古代文艺美学。邮政编码:231561・112・
第5期 历史上第一首悼亡诗的经典化历程——《江城子·景梦》接受视角的历史演进 2008年,活着的人是失落的,是孤独的,是寒冷的,是无望的。 ”3、文体的双重性。悼亡诗具有“读一遍变色,读二遍泪流满面,读三遍心碎”的艺术感染力,但凡事都有过犹不及或过少的时候。顾贞观对纳兰性德悼亡诗有批评:“容若的诗有一种凄婉婉约之感,使人读不完。”而苏轼的诗恰恰把握了情感的度,诗人通过双重文体来实现。从内容上看,这首诗的确是一首婉约的诗,但诗人用豪放的文体来表达婉约的内容。正如王水照所说:“全诗情感深厚,婉约深邃,文笔来去匆匆,场景不断变化跳跃,却又令人流连忘返。……豪放的文笔和思考的力量,默默地运用在婉约的情境中,因此很感人。”就情境而言,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婉约的诗; 从写作和思考的力量上来说,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首大胆的诗。 ”所以苏轼的诗不只是凄婉悲怆,而是让读者在苦难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元代剧作家白朴的悼亡诗《木兰花岭》用大胆的语言表达了悼亡的内容,诗人看到香囊,感动不已,悼念亡妻。诗中豁达的语言相互呼应,如“西风映梅”一诗,呼应了“西风楚辞曲终”;“疏影斜斜,谁家清香飘来”一诗,呼应了“我期盼香魂飞向蓝天”。这种豁达的语言,既表达了缠绵凄婉的痛苦,又避免了读者在痛苦中感到绝望,反而让读者在凄婉处体会到一种心灵的震撼。
4、意象的独特性。中国传统悼亡文学中,作品追求亡妻的“善”,亡妻形象因此定型。清人沈德潜认为“越是琐碎,越是真实”。而苏轼的诗中,诗人不从琐碎小事入手,而是在开头抒发真情实感,进而捕捉亡妻的美貌,“小窗处,梳妆打扮”。亡妻的美貌早已定格在诗人心中,即使岁月冲刷也无法改变。这种对“美”的追求不同于一般悼亡作品对“善”的追求,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的美。如果借用西方的美学观念(外国诗歌中的女性注重“美”)来审视古代悼亡作品,苏轼这首诗的价值就更加独特了。 苏轼诗中对“美”的追求,在龚自珍的《琅琊沙书院》中是“注脚”。在龚的诗中,诗人竟把“看君梳头”作为自己一生的愿望之一,表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爱情。这种写法,不就是《小窗里,梳头》的翻版吗?诗人用了非常纯粹的句式,不同于柳永诗中的情色描写,避免了审美情趣的庸俗,而显示出高雅。5、曲调的多变性。苏轼的《江城子·景梦》诗除了内容上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外,在形式上也是别具匠心,尤其在曲调的多变性上,这种多变的曲调,是为了适应悼亡诗中悲凉凄婉的情绪变化的需要。 夏承焘评价:“《江城子》全诗调式为平韵;三、四、五、七言句的运用和选择错综复杂,韵律和谐,起伏不平,容易写出平和而复杂的情感。”
这一转调给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艺术冲击。宋代邓肃的悼亡诗,就模仿了苏轼的调调。诗中是这样的:“酒过三巡,执手过廊。夜渐凉,月如霜。笑问桂花,何时散发天香?将一枝插在帐中,云雨归来,自有清香。如今雨水漫天,绕堂而过,自有清香。不见堂上执手的老鸳鸯,已伤秋色,夜渐长,钟声悠长。”诗人被此景所感动,以追忆往昔的方式,表达了对亡妻的哀思。桂花遍地,昔日执手而行的老鸳鸯却不见了。 一种物换人换的凄凉之情被生动地再现出来。这首诗虽然没有摆脱悼亡作品“见物思人”的写作标准,但诗人大胆地借用了苏轼诗的曲调。悼亡诗在宋代迎来了春天,如王衍的《木兰花漫》、石大祖的《守楼春》、李元英的《查瓶儿》、张澍的《浣溪沙》;就连诗人刘克庄在《后山集》中也认为:“悼亡作品,前有潘启圣,后有魏肃,后有李彦虎,不可再加。” ”但他也有两首挽歌,《松风记,写于福清路上》。宋以后,挽歌不断发展,如金代元好问的《雁丘》;清代朱彝尊的《高阳台》、周之崎的《蓝衫透湿》等;近代,乔大壮、陈增寿、唐圭章等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令人动容的挽歌。2800年艰难的接受历程对于古典作品在后世的审美命运,接受史专家陈文忠教授曾指出,大致有三种情况:“一是流行一时,后来却消失了;二是被历史选入后,被视为经典。
但这样的作品往往成为如马克·塔夫茨所说的“人人都希望读过,却没有人愿意花心思去读的书”(《文学的消失》);第三,它们不仅在过去很流行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很流行,成为各个时代接受的热点。”苏轼的《江城子·寄梦》就属于第二种情况。学者陶文鹏认为:“在怀念和哀悼中,作者融入了自己坎坷、失意的人生经历的感受,使诗的情感和意义更加深刻,所以被古今评论家誉为史上第一首悼亡诗。” ”陶渊明的结论只说对了一半。这首诗的确被当代评论家视为千古绝唱;然而,古代评论家对此诗却十分冷漠。在其从宋至清近800年的接受史上,评论家很少提及这首诗,即使提及,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评说。如傅藻云说:“二十日,录梦,作《江神子》(《东坡纪事》)。苏轼弟子陈师道认为:“有声当达天,有泪当达泉。”然而,“通史第一人”陈师道的精辟结论,在漫长的历史接受过程中,并没有得到回应。与词评论家的冷漠相比,选集家们更是无情。宋代黄易的《唐宋先贤佳词选》; 卓人悦的《古今词评》、清朱彝尊的《词总集》、万澍的《词录》等选集,均收录了王衍、石大祖、李元英、张恕、元好问等人的悼亡诗,苏轼追悼朝云的《西江月·梅花》也被收录不少。唯有《江城子·记梦》词人保持沉默,甚至“残忍到底”,众多选集均无一收录,成为词人心中的“遗忘角落”。
评论家的“惨烈努力”、选集编撰者的“冷漠”,使得苏轼《江城子·梦》八百年来接受过程如此艰难,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。1、悼亡文学的独特性。悼亡文学种类繁多,本文仅讨论诗、词两种取得最大成功的文学体裁。悼亡文学相较于其他题材的文学,有其独特之处。悼亡诗词是文人的情感纪念,因此从创作者的角度看,只有丧妻的经历,才最能写出如此痛彻心扉、感人肺腑的作品。从接受者的角度看,最能与小说产生共鸣的,是那些经历过妻子去世的人。 明代学者李开先在悼亡文学集序中表达了这种体会:“我过去读悼亡文学,即使有些很痛苦,我的心也不为所动,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。我的妻子张义仁去世后,我重读这些作品,眼泪止不住。”从选集编撰者的角度看,元代方回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观点:“有生就有死。悼亡、悼词,以及一些悼词,都是尽伦理规范之用,也蕴含着忠孝悌之义,读者不应畏惧或憎恨。”选集编撰者选择的标准,不能不考虑到读者的感受。选集编撰者和读者的双重制约,使悼亡文学在彼此的碰撞中,接受变得越来越艰难。古人对悼亡作品也有着严格的要求。 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中指出:“即便是悼亡诗,也必须缠绵婉约,才算绝世佳作。”在这些内外的多重批评之下,悼亡文学必然会影响到它的接受过程。2、悼亡诗的古典性。在我国历代悼亡作品中,潘岳的《悼亡诗》、元稹的《遣悲三首》成为悼亡文学的典范。潘岳是最早以悼亡为题材的,全诗都是悼亡妻子的。 它围绕着妻子一生的琐碎小事展开,并把强烈的悲痛融入这些回忆之中,如“望屋想她,进房想她经历的”、“香气尚未散去,残垣断壁还在”等等,常常被后人用来悼念。
《鸡西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5期,许多关于逝者的作品,或照搬句式,或借词,成为悼亡诗遵循的规律。诗评家也对这首诗给予了认可,钟嵘、钟惺、沈德潜等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明代孙况在《文选注》中评论道:“写得诚恳,曲折离奇,读之令人欲死,即是平凡的文字,也十分精彩。因其文能应情,用词适度,格调比悼亡诗更胜一筹。”这些评论家的评论,促进了这首悼亡诗的接受。如果说潘岳的系列诗为悼亡文学带来了一种普世的写作风格,那么诗人元稹的《送悲三首》则将悼亡诗推向了顶峰。诗体为七言律诗,语言朴实。 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平淡的描写手法,在追忆往昔、哀叹当下的氛围中写作,把血泪的悲痛化作深情的诗行。诗论家尤爱此诗。孙素认为“古今悼亡诗何其多,而无一能逾此三首,以浅显易懂,故不为人所理。”陈世荣在《求知居唐诗选》中甚至说:“此首悼亡诗为最佳。”即便如此,悼亡诗的经典化还是延续了千百年来。潘岳、元稹规范了悼亡诗的写作,悼亡诗成为悼亡文学的准则。历代诗歌总离不开“身外之物,儿女情”,诗中亡妻的形象也多为“善”,如勤劳、善良、体贴、贤惠等。 这样的原则一代代流传下来,形成了选择和批评的标准。另一方面,苏轼的《江城子·景梦》这首具有异常特征的诗,在古典悼亡诗阴影的“庇佑”下,确实不易成长为“参天大树”。
3、苏轼诗歌的多重超越。陈寅恪评价元稹《送愁三首》认为:“皆只写他清贫处世,操持家务……对贫苦夫妇写得实事求是,无一言过其实,情与文皆佳,成为千古绝唱。”悼亡诗着眼于生活的琐碎,而苏轼的《江城子忆梦》中,妻子不仅是生活伴侣,更是知音;诗中的情感不仅有丧妻之痛,也有知音的叹息。在亡妻形象的塑造上,前朝亡妻形象着眼于其“善”的一面,而苏轼的诗歌则更着眼于“美”的形象,这种有悖常理的形象势必会受到“歧视”。 在写作风格上,苏轼的诗也有自己的特点,即以思念某人的方式,表达对亡妻的哀思。这些多重超越,给作品戴上了无形的枷锁,延缓了其成为经典的进程。3、百年来的“经典化”过程《江城子·忆梦》直到20世纪才迎来接受史的“春天”,从一首无人问津的诗篇,成为一首著名的悼亡诗。学界不断发现“此宝”的无限价值,评论家对其推崇备至,选集家尤爱选注,相得益彰,最终将这首诗推为“千古悼亡诗之最”。 第一个关注《江城子·梦》这首诗的选本是朱小藏,他在1924年编纂的《宋诗三百首》中将此诗列为代表作;20世纪60年代胡蕴逸的《宋诗选》和70年代龙玉生的《唐宋名家诗选》均选编并注释了这首诗; 20世纪80、90年代的大量宋诗选集,如唐圭章《唐宋诗略说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《唐宋诗选》、张彰《历代诗集》、吴雄鹤《唐宋诗选》、顾逸生《宋诗精粹》、郭延泉《历代诗今译》等,都无一例外地收录了这首诗,有的还在选集中对此作了阐释。
苏州学界对这首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认可。学者们从主题、地位、风格、基调等方面对这首诗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,加深了人们对这首诗的认识。1、主题的多元性。关于这首诗的主题,学界提出了多个合理的主题,无论是“真情怀怀说”、“壮志未酬悲愤说”、“执着追求理想说”、“改革之痛说”,还是“现代个人爱情说”。胡蕴仪认为“这是一首悼亡诗,体现了作者对妻子永志难忘的深厚感情”。胡从诗本身的情感基调入手,因为诗人与亡妻已分离十年,时间之长,千言万语化作万滴泪水,诗人的真情浸润在万滴泪水中。 如果我们跳出诗歌本身的束缚,从诗人创作此诗的背景来分析,诗人是在京城外出使时写此诗的,政治上是孤独的;诗人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妻子,自己也是孤独的;而诗人所处的密州山城的环境更是孤独的。在这种寂寞中,亡妻成了最好的交流对象。因此,陶道树认为:“苏轼的悼亡诗,是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和打击,难以实现政治抱负的结果。他怀念曾经与之共处的亡妻的美德,于是心中充满悲愤,通过梦境充分而克制地宣泄出来。”苏轼悼亡诗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一般以见物记人、叙旧记事的写作风格,而是把亡妻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,与亡妻进行交流。 亡妻不仅是他单纯的知己,更是他可以相互交流的人生知己,诗的内涵尤为丰富。正如艾志平所说:“全诗贯穿始终的深沉情感,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亡妻的真挚怀念,也表现了作者对某种理想的执着与追求。”
”此外,还有王文龙的观点:“词有力地证明,即使在封建制度内部,也存在着从一夫一妻制发展起来的现代个人爱情。”另外,周汝昌认为“苏东坡悼亡诗是一首抒发改革之痛的诗”的观点,也有其道理。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首诗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,可谓“人人有己”,如此多重主题的发现,更增加了这首诗的深度。2、词境界的开拓性。从悼亡诗过渡到悼亡词,并非易事。日本学者村上哲贤指出:“这种所谓‘悼亡’的主题,在诗歌上,自金代潘岳以来,一直保持着,但在词方面,在苏东坡词之前,找不到有同样目的的作品。” 悼亡妻之情可以说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怀,但从宴饮娱乐起家的词却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这种情怀纳入其中。“苏轼把悼亡主题融入到自己的诗中,使原本只承载着宴饮娱乐、妆花香的诗担负起了一种不属于自己的使命,那就是把死亡这个悲壮的话题嫁接到诗歌主旋律这个小路上去,这的确是诗境界拓展的一大创新。”刘乃昌认为:“以诗来悼亡,是苏轼的首创,显示了作者拓展诗境界的开拓精神。”王宝桢也持类似观点:“苏轼的这首诗,是诗歌史上第一首悼亡诗。” 诗中悼亡题材的选择,拓展了诗歌的境界,是苏轼拓展诗歌境界的例证之一。”朱景华也认为:“这首诗虽然优美,但却是苏轼作为‘悼亡诗’所创造的。
...以词悼亡妻,是苏轼的首创,也是词史上的第一次。 “人们谈及苏轼的词,尤赞其豪放,使词具有阳刚之气;其实,这并不完全正确。苏轼婉约的词,也有许多突出的特点。挽词是苏轼开创词境界的最好例证。”3、情感的复杂性。从诗人“相望无言,唯有泪流”的艺术表现,到“读罢无言,唯有泪流”的审美效果,这首词为何如此感人?这与词中情感的复杂性分不开。翻看古代悼亡诗词,无一不在缠绵悱恻、怨声载道中上演悲剧,但苏轼的挽词却颇为独特。全诗没有一丝琐碎,而是通过“梦”将全诗分为三个阶段:梦前、梦中、梦后。全诗表达了对苏轼身世的哀悼。为死者哀悼,这比Xia Chengtao的哀悼更重情绪混合在一起,所以这首诗:“朴素,但持久,持久。”